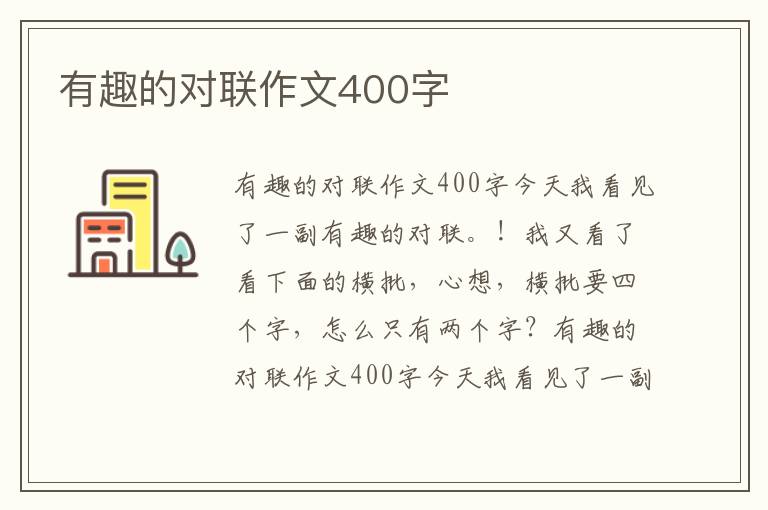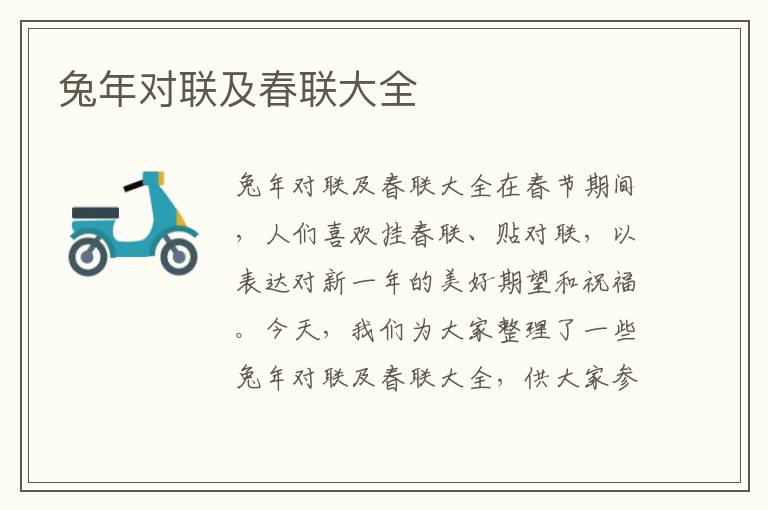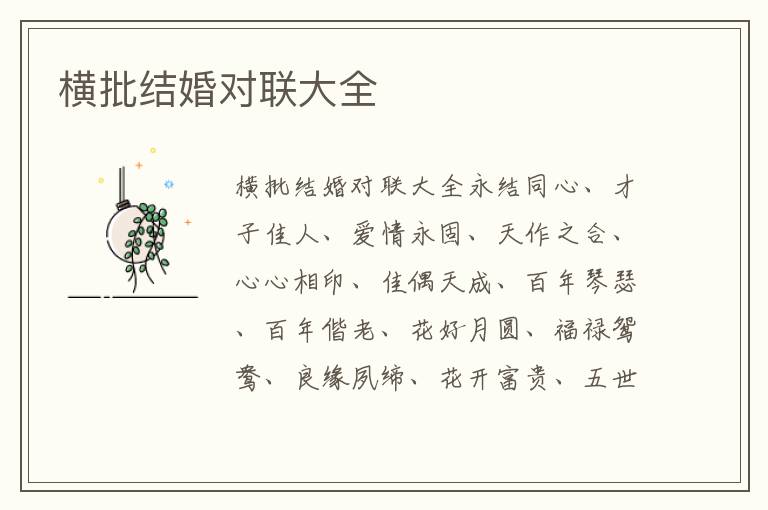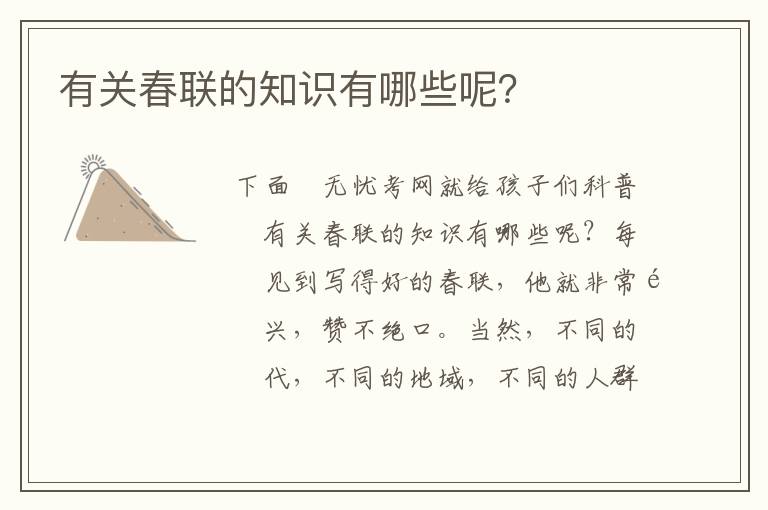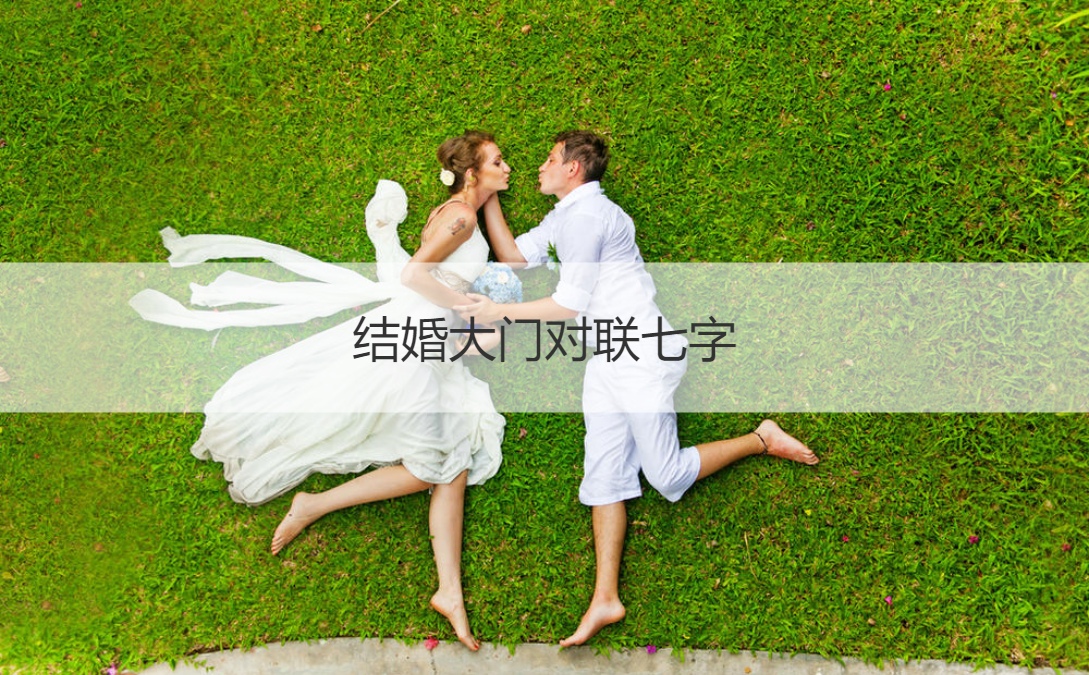【万安山下】春联芬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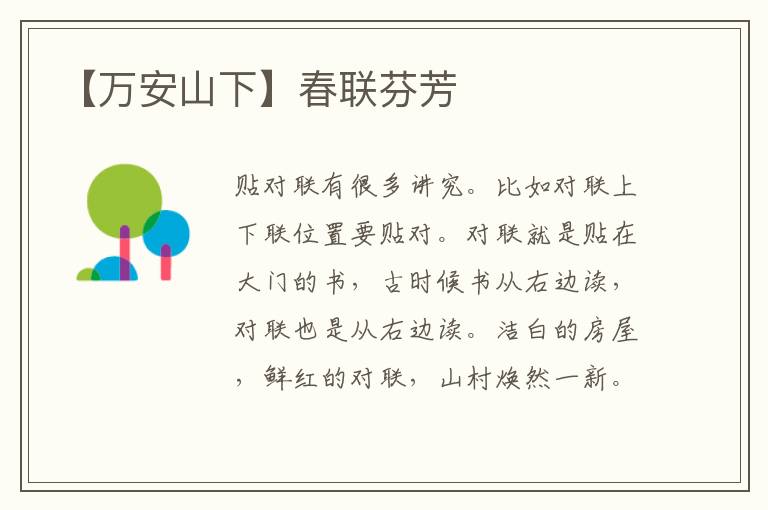
点击开门
点击开门丨打开动画
一场大雪落在了瓦屋上,土墙上,皂角树上。门前的石碾变厚了。旷野里的麦秸垛胖成了巨蘑菇。大地苍茫安然,南山隐而不见。
乡村在稀疏的鞭炮声中,等着火红的春联梅一般盛开,点缀这盛大的银毯,隆重迎接即将踏着银毯迤逦而来的春节。
村路上,赶集回来的人拧成了绳。手提着,车载着。在花花绿绿的年货上,常有一卷红纸细细地卷着,用红绒绳系着,放在最上面。
红纸买回来,一一裁好,要请文化人来写。学校的明灿老师会选一个晴朗的日子,在校园里支起桌子,为老师和乡邻写联。桌子上摊着一本书,看一眼,写一副,不一会儿,满地都是写好的对联。“勤劳人家先致富,向阳花木早逢春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睦邻孝老乡风美,重教读书家运长”……墨汁的气息弥漫在校园里,飘荡在老槐树的树枝间。树上的小鸟跳了几跳,挂在槐树上的打钟绳轻轻地晃悠。
父亲买的也是红纸,年年自己写春联,虽然他认为自己的书法很一般。父亲一般在卫生室写,铺得开摊子,也方便有人拿着红纸来找他写。一写就是半天,回家来的时候,衣服上还带着墨的味道。
“二十八,贴花花。”旧对联铲去,新对联登场。每副对联都是各自卷在一起。父亲小心展开,读读内容,才在门框上涂抹浆糊,贴上对联,用小笤帚轻轻扫平。大门上,厨房上,牛槽上,枣树上,到处红艳艳的,真是满院春光了。
贴对联有很多讲究。比如两扇门上的门心,其实就像两个人,字多的一排是身子,字少的一排是手。身子要靠着门轴,像兄弟作揖,互敬互爱,不能反贴门神,互不搭理。比如对联上下联位置要贴对。对联就是贴在大门的书,古时候书从右边读,对联也是从右边读。上联飞流直下,下联春水向东。说到“下”字时,他的手往下一砍;说到“东”字时,手平着推出。这个手势至今让我印象深刻,也让我对“仄出平收”的格律有了朦胧的理解。
雪花无声地飘着,轻盈的身姿掠过树杈和房屋,窥视着红红的对联,天地之间,一片祥和。
过年了。鞭炮声响着,孩子们笑着跑着。洁白的房屋,鲜红的对联,山村焕然一新。吃过饺子,父亲带着我们逛街,看人家大门上的对联,写得好的背下来。
父亲写的春联与别人有些不同。梨花院落溶溶月,柳絮池塘淡淡风;沾衣欲湿杏花雨,春面不寒杨柳风;兴家必种书中粟,立业须耕砚上田;惜花春起早,爱月夜眠迟……这些句子挂在门边,过来过去,有意无意就会看两眼。总感觉每一联都是奇妙的画,每粒字都是值得回味的糖。
等我也能分清上下联了,父亲就把贴对联的工作交给了我。有时还让我收集对联,过年他来写。于是,抄联成了我的习惯,慢慢竟集了几个小本子。
后来,印制对联纷纷飞上门楣,闪着光,印着花,一看就喜气洋洋,富贵逼人,内容多是“生意兴隆”“年年发财”之类的话。可父亲依旧自己写联。有年弟弟嫌寒酸,专门买了送回来,父亲也只在大门上贴了一副,家里,依然是手写的对联。为了不太落伍,他也会用金粉来写。他说印制的对联是好看,只是少了墨香。
墨香?从我实际的体验来讲,墨汁的气味与“香”实在不搭边,甚至已站到了对立面,但赞成父亲手写春联。因为那些联句仿佛奇妙的种子,常常在心中悄悄萌动着春的绿意。
有年春节,洛阳晚报举行了一次征联,要求在相同位置嵌入“晚报”二字,首奖是一台液晶彩电。觉得有趣,就编了两句发过去:“不论早春晚春,伊洛时时景色好;且看网上报上,嵩邙处处牡丹新。”没想到幸运降临。把电视给父母送回去,家里来亲戚,虚荣的父亲总要拐弯抹圈说到彩电上,还拿出印有照片的报纸给亲戚看。
前些年,古村落魏坡举行征联比赛,获奖的对联挂在了大门上:“今洛水,古雒水,雒水即洛水,洛神出洛水;先魏坡,后卫坡,卫坡承魏坡,魏紫源魏坡。”父亲专程坐车去了一趟魏坡。他说太阳照着大门楼上黑底金字的联匾,他闻到了木匾的香,还有墨的香,真的很香。我相信他说的话。好墨,不同于化学墨汁,的确是能闻到香的,不仅因为那对联与他女儿有关。
这两年,临近春节,单位里就会专门组织大家自拟内容,手写春联,内容也多与家风有关,与读书有关。书写时,办公室里红联灿灿,笑语喧喧,墨香缭绕,春意盎然。
在印制春联很容易得到的今天,手写春联重新承载起文化的传承和家风的熏陶,不仅不觉寒素,反而成为一种时尚。越来越多的人家贴上了手写春联。从街上走过,大门上的手写春联,仿佛身穿粗布大缯的读书人,自有一种腹有诗书的儒雅,一种诗礼传家的气度,一种波澜不惊的从容,一种脉脉流溢的芬芳。
作者 | 陈爱松 编辑 | 刘璐 总编 | 张晓晨